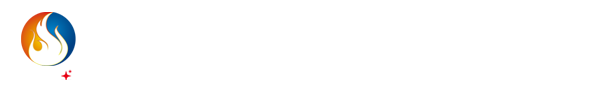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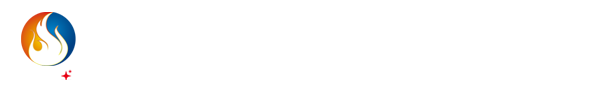
倡导一种对待国学的理性态度
我们当前所能做的,当然不是“反传统”和“斥儒学”,而是对于国学中与宗法专制权力密切相关的礼教和国学中具具有普世价值的永恒成分加以区分,既发掘国学中所包含的“中道”、“和谐”、“忠恕”、“节欲”、“兼爱”、“非攻”等等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又不要试图将已被证实无法促进历史前进的制度化儒学再次扶上神坛。
西方的历史已经终结。这是由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不少人所得出的结论。的确,这场尚未完全过去的危机显示出整个西方工商文明确实已经遭到巨大挑战,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主流经济体系的正面价值看来已碰到巨大问题,西方的生活方式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探索新文明新道路,设计新的经济体系的任务,已经历史性地摆在了人类面前,特别是摆在了思想界面前。
在西方文明陷入窘境的同时,近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的不间断的高速发展,适时地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前行的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中国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最大动力。世界再次瞩目于东方,瞩目于中国,于是,在耶稣之外,人们又一次看到了孔子的光辉。
也许是出于文化的自觉,也许是出于对历史的反拨,近30年特别是近20年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同步,一股国学热相伴而来,一浪高过一浪。各著名高校近来纷纷设立儒学院和国学院等传统文化机构即是明证。
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对中国文化,对国学作出了非常乐观的估计,走向极端者则认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在笔者看来,如同以往的反传统曾经丧失了理性一样,当前的国学热似乎也失去了冷静。在这个背景下,倡导一种从容理智的境界和立场,非常必要。
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沐浴着当代文明的学者,在这时,我们似乎更应该对中国文明持一种审察和反省的态度。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其存在的基本价值,今天看来主要是为了应对一个短缺社会、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它的全部设计,它的基本原则都是为此而来。如何使一个短缺社会能够正常运转,是中国的历代思想家们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中国文化的核心为何是秩序、是义务、是群体、是家族,而不是权利,不是个性,不是自由,就在于它所维系的,是一个短缺社会的基本秩序。
如何在短缺型社会维护公共管理机构正常运行?如何在物质匮乏的基础上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孔子给出了一个历经两千多年始终有效的答案,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原则首先要求的是物质生活资料的分配以尊卑等级为标准,而《论语·颜渊》中对这条为政原则的理解,也正是落实到了食物分配的现实层面上,齐景公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物质生活资料分配按照尊卑等级为原则,又反过来使以衣食、车马、居所等为代表的物质财富,成为尊卑等级的标志,以便于“ 别尊卑,明贵贱”,也正因此,历代正史才会把《 舆服志》当作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而家庭乃至家族中的物质分配,则由“孝”来加以规定。“ 孝悌者,其为人之本”,孝,不仅意味着“能养”,还意味着要“能敬”,唯有“能敬”,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能养”,最大限度地保证家庭内部的财富分配向长者尊者倾斜。
当社会文明进化到一定阶段,工商文明显然比农耕文明更有利于物质财富的创造,早在西周时期的姜齐,就已经意识到工商文明对于富民强国的巨大作用。然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隐含着尊者贵、贵者富、卑者贱、贱者贫的物质分配逻辑,而有利于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商文明,则会在民众中创造出大量财富与身份地位不相称的富有者,卑贱者比尊贵者更富裕,就可能“ 僭上”,可能“八佾舞于庭”,可能“礼崩乐坏”,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就会遭到破坏,于是历代王朝,都不约而同选择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生长于短缺型社会中的国学,它的基本使命本是要维护短缺型农耕社会的秩序,并且为之提供不断的理论支持。
社会要获得协调和稳定发展,有两条路径:或者使物质财富极大涌流,最大限度地满足各阶层日益增长的生活欲望;或者抑制人们的生存欲望,以适应物质的匮乏。既然前者被否定,那么就只能选择后者。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能义者,利败之也”,乃至“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成为国学中的主流观念。
如果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社会财富分配上规定了地位与财产一致的原则,那么在道德与权利的关系上,则规定了君有君德、臣有臣职、父有父权、子有子份的道德与权利相一致的原则。统治者的道德成为其权利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这也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逻辑所在。当然,对于被统治者来说,这一逻辑则变成了被统治者身修、家齐,统治者便可以国治、天下平。于是,传统社会的人们,总是将海晏河清、天下太平的希望寄托于内圣外王的君主,而不是寄希望于发展完善促进社会发展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国古代社会讲究的是德治、礼治、人治,而非法治。
那么,曾经阻碍了工商文明发展的儒学,是否能适应后工商文明?当遭遇了金融危机重创的西方人,将目光投向古老的孔子时,儒学能否为西方提供一个救世良方?21世纪会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吗?很显然,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序列中,后现代貌似前现代的精神复归,然而其间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或许,新教伦理假“上帝”之名为无孔不入的赢利活动作了“恪尽天职”的辩护之后,清教约束却无法扼制市场经济主体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无限贪欲,而古老中国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欲望、伦理的理论,可能会为西方、包括为人类设计新的文明模式提供借鉴。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一体、文化多元的世界中,靠西伯行善,国人让耕,从而感动虞国、芮国不再争田的儒学神话,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历史前行的另一条路线。
今天,中国的崛起的确需要中国文化的支撑。民众及大众传媒的国学热,表达了物质生活丰富之后的人们对于精神家园的渴求,而知识界在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时对于文化主体性的呼唤,都无疑构成国学热背后的客观因素。传统不可能完全被割裂,“五四”运动迫使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走下神坛,但作为思想学说的国学,依然是我们宝贵的思想资源。就儒学来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三纲”维护的是宗法社会的尊卑等级与社会秩序,但“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反映的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德操,前者理应遭到唾弃,后者却依然具有普世价值。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当下的中国都已被无情地抛入全球经济体系中,这时,你不想现代化都不行,现代化已变成铁的历史必然性。然而,中国人的“价值”与“精神”却无法被同步一下子置换。“历史”变了,“价值”却无法同步跟进。“历史”与“价值”的冲突就这样正在撕裂当下的中国。这样,我们一方面生活在现代和“市场”之中,另一方面,我们的精神和情感又与古老的“义利”观等相连。在这种情况下,国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当然就成为问题。我们当前所能做的,当然不是“反传统”和“ 斥儒学”,而是对于国学中与宗法专制权力密切相关的礼教和国学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永恒成分加以区分,既发掘国学中所包含的“中道”、“和谐”、“忠恕”、“节欲”、“兼爱”、“非攻”等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又不要试图将已被证实无法促进历史前进的制度化儒学再次扶上神坛。